目录
快速导航-
特别推荐 | 明月,初见与同心
特别推荐 | 明月,初见与同心
-
特别推荐 | 以病为师
特别推荐 | 以病为师
-

特约专栏 | 在西西里岛寻找巴洛克
特约专栏 | 在西西里岛寻找巴洛克
-
作家视野 | 向日葵
作家视野 | 向日葵
-
作家视野 | 记事簿:江南
作家视野 | 记事簿:江南
-
作家视野 | 耳鸣者手记
作家视野 | 耳鸣者手记
-
作家视野 | 漫游者或异乡人
作家视野 | 漫游者或异乡人
-

别具只眼 | 语文哦,我的语文
别具只眼 | 语文哦,我的语文
-
别具只眼 | 野狐坡
别具只眼 | 野狐坡
-
别具只眼 | 太极人生
别具只眼 | 太极人生
-
别具只眼 | 花有重开时
别具只眼 | 花有重开时
-
人与自然 | 风吹草低
人与自然 | 风吹草低
-
人与自然 | 太姥山笔记
人与自然 | 太姥山笔记
-
性情写作 | 南望
性情写作 | 南望
-
性情写作 | 老物件
性情写作 | 老物件
-
性情写作 | 乡村旧事
性情写作 | 乡村旧事
-
海天片羽 | 一个活成菩萨的人走了
海天片羽 | 一个活成菩萨的人走了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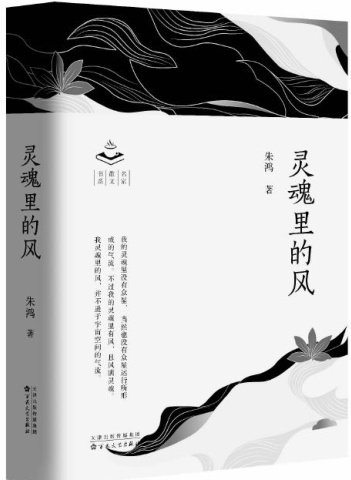
海天片羽 | 竹杖芒鞋轻胜马
海天片羽 | 竹杖芒鞋轻胜马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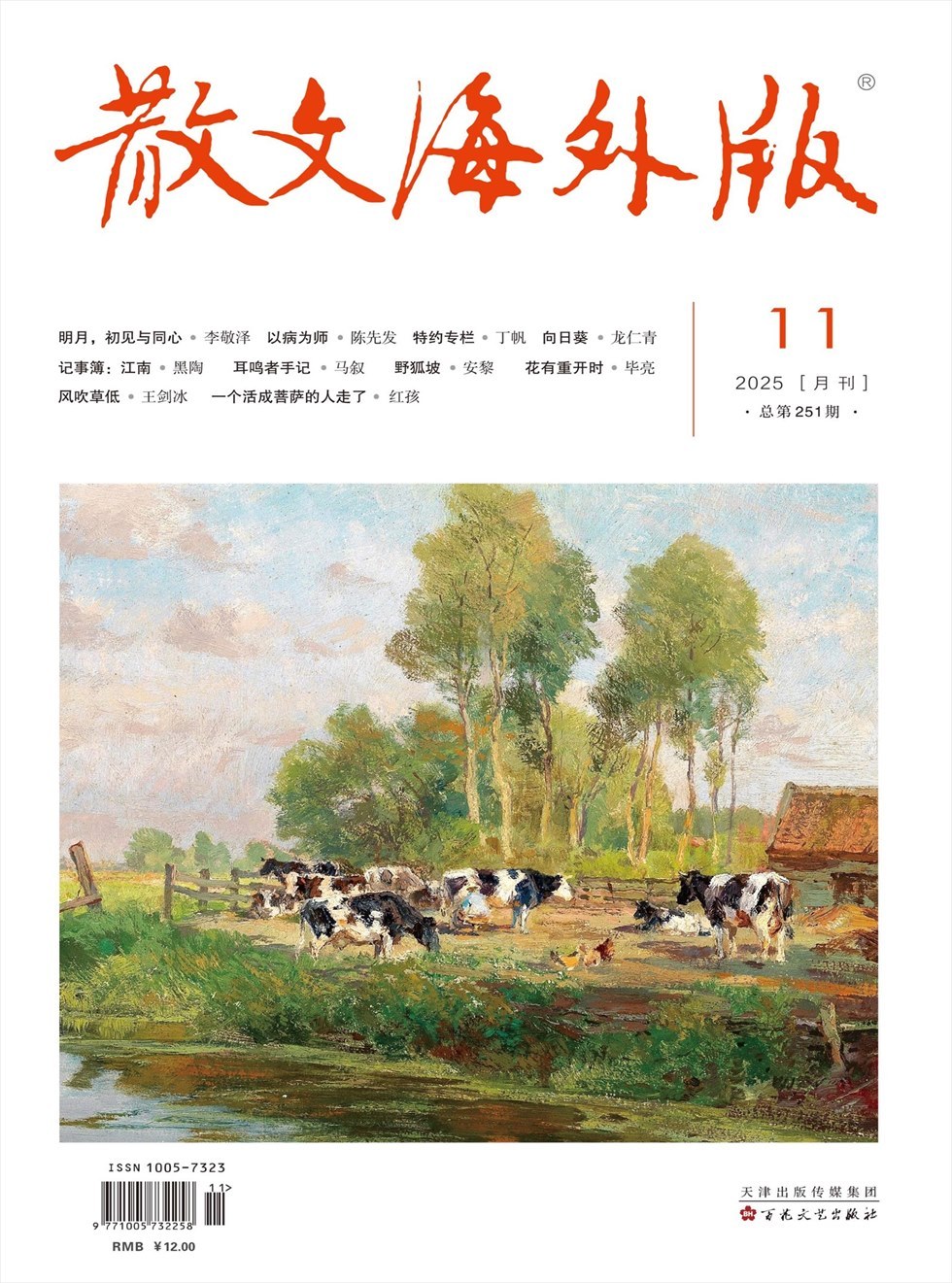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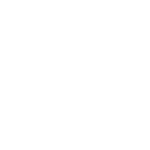
 登录
登录